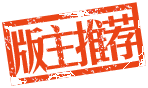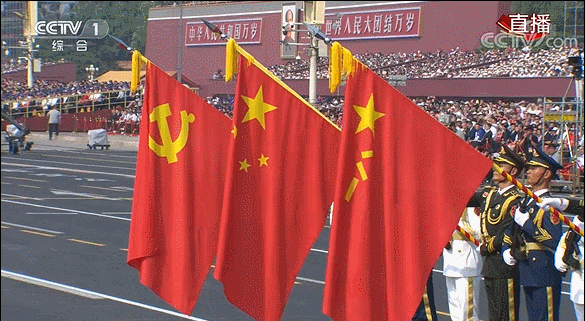临行前,士兵们和村民们都来送他,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深受喜爱的年轻人为什么要突然离开。哲德把他的仇恨深埋心底,而非挂在嘴上。士兵们送了一把短刀和几杆标枪给他,“这里的道路到处都游荡着劫匪和盗贼,空手出发就等于自寻死路。拿上这些吧,万一碰到了那些恶狗,就向他们展示一下我们教授的武艺。”村民了也凑了些熏鱼、小麦和面包,索里克给了他一些钱币,作为路上的花费。哲德接受了,很感谢他们的好意。 哲德往南走,不久到了一个渡口。莱茵河在入海处变得十分开阔,形成了非常广阔而肥沃的一片河口三角洲。丰沛的水流夹带着跋涉千里的泥沙,奔流至此,变得缓慢而平静。数万年来源源不断的泥沙在此沉积,形成了许多沙洲、小岛。莱茵河也被这些小岛分割成众多支流。整个弗里斯王国建立在河海环抱中,其国土因这众多支流而变得支离破碎。肯莫尼城堡建在其中较大的一个沙洲小岛上,在其南面,通过桥梁与其它岛屿连接。它把守着王国首都的大门。要塞中居高临下的弓箭手俯瞰个整个宽阔河面,监视每一艘从此经过的船只。敌舰如果试图由此溯流而上,直达杜里斯特,则几个弓箭手就能让他付出惨重代价。而它本身雄踞孤岛,城墙之下便是水流,无法登陆攻取,只能从桥梁进入,可谓形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 哲德在渡口找到渡船,渡河进入了肯莫尼。这样重要的位置上的城堡,也不过是那时西欧常见的简陋的环形木堡——两米多的削尖木桩围成壁垒,离地一米多的高度上支起木架子用作士兵守卫的哨位,几座木塔。里面十几间小木屋,那是士兵的营房、武器库、粮草库、马厩等设施。中间有一座稍大的木屋,茅草屋顶上插着绿底红色三杈树枝图案的旗帜,那肯定就是雅尔的府邸了。“真是可悲啊!恢宏伟大的罗马帝国陨灭,其后继者却只知劫掠不知建设。文明科技被掷于火堆,他们毫不珍惜,反倒拾起金银珠宝这些石头。”哲德向城堡的守卫说明了来意,请他通报雅尔时,细细观察了这座城堡,不禁这样想着,“假如我得到了这座城,一定要用最好的石料来重建,把沿海沿河的塔楼建的又高又坚固,在上面安放罗马人的弩炮,这样才足以确保王国安全无虞呢。” 很快守卫出来,说雅尔同意见他,把他引入了府邸。这里显然比道琴嘉的那些穷鬼渔夫的小棺材要宽敞多了。虽然如果用一人高的长矛相接放在屋里的地面上,也就五六根就到头了。肯莫尼的侯多夫雅尔看起来是一个凶恶老辣的领主。他毛发旺盛,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遮住了半张脸,额头的皱纹又占据了另外半张。左脸有一道伤疤,从发际一直割到下巴,左眼也因此只能半睁着。另一只眼睛敏锐而机警,在眼窝里不时打转。他和其他维京人一样,长得高大壮实,穿着红色的衣服,即使在自己的府邸里,也披着半袖锁子甲。哲德不喜欢他,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。“可是,天下间又能在哪里找到一个好人领主呢?”他这样想着,也就释然了。 哲德很恭敬地行了礼。雅尔坐在他的宝座上,盯着他看了一会,用一种与他的体貌不符的想豺狼哀嚎般的尖细声音问道:“你是谁?”哲德说:“我叫哲德。很乐意为您效劳,雅尔。”雅尔说:“我并不放心把重任交给一个不受信任的人。因此,你还是直接说说为什么要来拜见我吧。”哲德说:“道琴嘉的索里克长老让我来找您,以请求您的帮助。”雅尔冰冷的语气缓和了些,他说:“噢,索里克是个好人,也是为数不多让我尊敬的弗里斯人。既然他派你来,那我会屈尊听听你的话。说吧。” 哲德长舒了一口气,现在事情有了一丝希望,他说道:“您听说过‘沃登里克号’吗?我和母亲一起乘着这条船前来这里,被牛颈斯温袭击了。”“啊,牛颈斯温。他的船队每年都来弗里斯勒索贡金,在我们还在凑钱时,他就停在外面的海域等着,把抢劫来往的船只当做消遣和小费。简直忘了,我们,弗里斯王国的统治者们,也是维京人。也难怪,我们的国王太软弱了。不过今年不会再这样了,我正集结兵力去围剿他。你所遭到的悲剧也不会再发生了。好吧,我还有别的事······”雅尔似乎不耐烦说了这么多,挥挥手示意哲德离开。 哲德听到这个消息,有些兴奋,他没想到报仇的机会来着这么突然这么快!他不顾雅尔的示意,急冲冲地说:“牛颈斯温也是我的目标,我想加入这场追捕!”“你的目标?你以为你是谁?你有多少人手和船只?”哲德感到胸口有一团火燃起,他变得激动了:“我的双手就是我的兵马,我的勇气就是我的船只!我们一定会杀死斯温的。”雅尔听完,冷笑了两声,又像乌鸦的啼叫一样吓人,他的确不耐烦了。“我明白了。你看我也很忙,你过一段时间再来找我吧。十年怎么样?”哲德没有被这嘲笑吓退,他不会让身负血仇的敌人死在别人手里,只有手刃斯温,才能解除他的丧母的痛苦。他严峻地说:“请允许我加入您追捕的队伍吧。我相信,像您这样的勇士,一定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复仇的渴望。” 这样的坚决似乎触动了雅尔。他想了一会,溜溜转的眼珠子盯着哲德,看的哲德全身泛起鸡皮疙瘩。然后雅尔说:“如果你真有那么坚决,那么向我证明你的能力吧。如果你是值得信赖的能人,我会让你有机会加入对斯温的作战的。”哲德说:“那请您委以重任来考验我吧。”雅尔用奥丁的标志洗去霉运,然后说:“我这里刚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道琴嘉的附近有一座修道院,他们请我裁决一宗土地纠纷的案子。说真的,我才不关心这些破事呢。不过国王希望取悦基督徒,防止他们造反。而我的人都在防备海岸,你就代表我去解决这件事吧。记住,要让僧侣们安静下来。我可不想激怒他们,那些秃顶们善于鼓动对维京人的反抗!”哲德回答道:“感谢您的信任,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”雅尔点了点头,让他退下了。哲德要出去时,他又补充了一句:“记住,不要激怒僧侣们。” 哲德离开肯莫尼后,过了桥梁,到了一个叫肯莫尼特的村子。他想了解一下这个王国,所以没有从渡口回去,而是绕了远路。村民们给他指路,使得他很快往东走到了王国的都城杜里斯特。杜里斯特是一座贸易城市。它在莱茵河上的港口连接着法兰克王国和丹麦王国,不列颠诸国,商旅众多,富庶繁盛。哲德在这里歇了歇脚,吃了点面包、熏鱼。然后就走了。 在城外的大路上,哲德看到了一支浩大的队伍。足足有三四百人,都拿着各种武器,有些还披着重甲、全副武装。这支队伍排成两行行军,占据了狭窄的道路两侧。有些人举着红底三扭纹的旗子,这是和杜里斯特城头插的旗子是一样的。哲德从仪仗中确信这是国王的队伍无疑,急忙停在路边,等待队伍的通过。队伍中间的正是弗里斯王国的统治者,罗里克国王。他骑着一匹骏马,周围簇拥着骑马的和持盾步行的装备精良的武士。他还是一个年富力盛的中年人,面白无须,留着金色的长发,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。他穿着附上珍贵皮毛的覆盖全身的深色链甲,戴着金光灿灿的王冠,正挽着缰绳缓缓行进,不时向路边单膝跪地行礼的臣民们挥手致意,包括哲德。作为一个国王,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仁慈的亲和力,而非威严的压迫感。 等国王的队伍离开后,哲德再次起程。他通过杜里斯特附近的一座桥,回到了莱茵河的北岸,然后往西,想回到道琴嘉附近找那个修道院。然而他人生地不熟,很快偏离了正确的道路,进入了一片小树林。这里长着许多参天大树,层层叠叠的树荫遮住了大部分阳光,使得林下阴森冷清。哲德走着走着,凄冷的环境使他感到不安。他解下背负着的标枪,选了四根拿着,小心翼翼地走进树林的深处。忽然在这片阴暗中他看到了一团火光,他即刻趴伏在林中深草处,提防可能的危险。仔细看时,原来是一堆篝火。边上有几个男人在围着烤火。初春的西欧,还是冷的恼人。有一间小木屋,屋外放着些斧头、刀剑、标枪、盾牌。这是林中的一处峡谷,两边的高地上,树木后面,草丛深处,都隐隐约约藏着几个人。这看来是某些人藏身的基地。哲德看清楚后,慢慢地从原路退出去,悄无声息,甚至屏住了呼吸。无论善恶,他可不想招惹这帮见不得光的人。然而他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枯枝,“啪”的一声大响,浪费了他的全部努力。那些人很警觉,他们一边喊道:“什么人?站住!”一边追了上来。哲德什么也顾不得了,马上拼命跑。就算树枝刮花了脸,藤蔓绊倒了好几次,他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步。开始后面还有几块石头追上来,后来就只有叫喊了。等到哲德一口气冲出树林时,危险就算过去了。 哲德在路边歇着的时候,遇到一群男女。他们衣着寒酸,面容沧桑,一看就知道是哪个村子的农民。哲德向他们询问情况。他们是多尔翰东村的农民。在杜里斯特的市集上卖出一些土特产后,正要回去呢。哲德于是跟着他们走,以免再遭到危险。农民们回到多尔翰东时,跟哲德说,那座修道院,叫卫利格罗波修道院,就在这儿和道琴嘉的中间,再往前走不久就到了。哲德谢过这些好心的村民,继续走下去。 没多久,路过另一座小树林时,在道路的拐弯处,哲德看到了三个男人坐在路边。他们一看到有人经过,马上站了起来,其中一个亮出了刀子,另外两个一手拿着投石索,一手拿着石子。毫无疑问不怀好意,哲德举起了标枪。一个男人说:“过路的,识相点吧。我们都是些穷苦的兄弟,不过是想讨口饭吃。如果你给我们一些钱,或者食物,我们就放你过去。如果没有,留下衣服也行。我们既不想伤人性命,也不想洗劫你的一切,就像维京人对我们做的那样。我流血冲突没有必要,只要你聪明点。”哲德说,举着标枪,他可不会因这番话放松警惕:“我也因为维京人的劫掠一无所有啦,穷苦的兄弟。可我宁愿和他们拼死一战,以雪仇恨,也断然不会沦为拦路抢劫的匪徒,洗劫另外的一些穷光蛋、倒霉鬼。况且我只有这一身破衣烂衫,包里只有几条咸鱼。我要是给了你们,只能饥寒而死。你们还是让我走吧。”劫匪说:“那就不要怪我们无情。你知道,维京人残酷的统治已经让我们丧失了怜悯之心。活在这黑暗时代里,人只能像野兽一样争抢无助的猎物。你若执拗不给,我们只好自己去拿了。”说完,他们挥舞投石索,投出石子。这些石子夹着呼呼的风声急速飞来,非常危险,其力道足以敲断骨头,打破脑袋。所幸劫匪们学艺不精,让哲德轻易躲过了。 哲德闪到一颗大树后躲避攻击。他有些紧张。“沃登里克号”上的战斗是他第一次和别人生死相博,而他败得非常惨,甚至没有碰到敌人就被打得半死。然而他很清楚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去面对一切,否则就不要再奢谈什么复仇大计了。于是他开始默诵圣经,激励自己。 劫匪们看到他躲到一边,马上追了上去。接近时,他们迟疑了。因为对手可能拿着标枪正在等他们探出脑袋。因此,他们也在树后藏好身体,迅速地往可疑的地方投出石子。几次试探都没有反应,他们确信猎物溜走了,于是冲了出来。哲德看到劫匪跑出来,一抬手就投出一支标枪,即可往后跑,躲到远离劫匪的树后。他听到了身后传来一声惨叫,有一个劫匪倒地了。他在痛苦地呻吟着,鲜血从他的食道里涌出,不时打断他的悲鸣。另外两个劫匪也躲了起来,哭着安慰受伤的朋友,并不敢贸然出来救助他。而且他们也知道救不了了。标枪在他的腹部捅了一个大洞,刺穿了他的胃。 哲德听到了他的战果。他变得兴奋,激动得难以平复。因为肾上腺素大量分泌,他已经感觉不到恐惧了。他跑了起来,从一棵树后跑到另一颗树后,慢慢地接近劫匪的阵地。两个劫匪不时出来投些石子,然而都没有击中那个疾奔的身影,反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。快接近时,哲德的步伐慢了起来,他悄悄地靠上去。这时林子里只回响着伤者的渐渐减弱的呻吟,没有别的一丝异响。这沉静让人恐惧,让人惊慌。 好一阵子了。忽然哲德就跳到一个劫匪面前,大喊了一声。这突然迸起的巨响震惊了劫匪,他慌了一下,才想起拔刀子,这时哲德已经把标枪扎入了他的胸膛。 另一个劫匪也被吓到了,他直接就转身跑了。哲德娴熟地投出一支标枪,扎穿了他的身体,把他钉在了路上。哲德确信危险解除了,一下子放松了,直接瘫倒在林中草地上。心跳的很快,很剧烈,怎么也止不住。当他歇了一会之后,感觉开始变得非常糟糕。他开始感到恶心,趴在地上把吃的熏鱼、面包全都呕了出来。他的头也变得剧痛,出现了一阵一阵的眩晕。哲德忍不住在地上滚来滚去,大叫大喊。 过了很久才他才恢复过来。然而依旧非常难受。现在他开始有一种负罪感,一种强烈的内疚。生命在眼前慢慢消逝,刚刚还那样鲜活的有灵性的人,马上就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。这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和冲击,足以让人内心长久地陷入不安。特别是对一个善良的人而言,或者那已是曾经。哲德尤其不能原谅自己的是,在他杀了那个人之后,他甚至感到了兴奋!这更令他恐惧,他害怕自己心中潜藏着罪恶的种子,害怕自己竟会喜欢上鲜血的腥臭味。这就是他第一次杀人,让他刻骨铭心。 哲德帮劫匪们收敛尸骸。他们犯了一些错,可是死亡已经足以抵罪,不能让他们还要受到曝尸荒野的惩罚。这或许也能带给哲德些许安慰。更大的安慰在后面。哲德在他们藏身的地方发现了许多衣服,染血的、破烂的、男人的、女人的。还有一些钱,一些食物,和几具来不及处理的男女尸体。哲德现在有些释然。杀无辜的人,和杀罪恶多端的人,感觉是不会一样的。他开始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,至少是一件正确的事,并且用这样的话来宽慰自己。 哲德拿走了值钱的东西,把受害者的尸体也埋了起来。忙完这一切时,夜晚已经降临了。哲德又开始担心害怕了。这些新起的坟墓很可能会飘荡出冤屈的鬼魂。于是他急忙逃离此处,口里含糊不清地诵着圣经里的语句。然而山上不时响起凄怨的狼嚎似乎更有现实的危险性。 不过幸而他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。当他惊慌失措地赶路,甚至顾不得自己跑丢的鞋子时,看到了新的灯火。他来到了一处用低矮石墙围起来的聚落。这里有精心开垦的田地,种着许多瓜果蔬菜。外面还有小麦田。道路修整的比其它地方更好,还铺上了鹅卵石。中间有一座小小的石砌的房子,上面安放着巨大的十字架。这里就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修道院了。不过他并不想在此时惊扰熟睡的僧侣们,于是在一堆干草里安心睡下来。 第二天,僧侣们发现了他,把他带到了院长那里。院长隔得远远的,质问这个臭烘烘的人的身份。哲德说:“肯莫尼的雅尔受到了您的请愿。现在我代表他来处理土地纠纷的事。”院长忙笑着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,说:“我还以为他会亲自来,或者派亲近的人来呢。”哲德并不喜欢修道院长,所有的修道院长,所以他没有坐下,依然站着说:“我也能胜任此事。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吧。” 院长拿出了一封信给哲德。上面写着漂亮的拉丁文,内容是某个领主将一块土地赠予修道院,结尾是一个叫福瑞斯威的人落款,还有几个证人的签名。院长说:“有一个三代以前的领主,承诺要把一块土地赠予修道院。我们的僧侣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他的这份手书。这自然是真实可信的,因为有好几个证人佐证。麻烦的是,现在这块地上住着一户人家,一户农民,宣称这是他祖辈传下来的土地。这当然是无耻的谎言。我们希望他们立即离开,让出那块地。” 哲德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些把戏。他在另一处修道院长大,看惯了这些圣徒的诡计。他故意问道:“请问那个叫福瑞斯威的领主是谁?他是哪个家族的?他的领地在何处?”院长有些支吾,似乎没有想到雅尔的代表会问这些问题,说:“当然,嗯,这是一份古老的文件了。嗯,说实话,我们并不认识这位,嗯,高贵的领主。不过这封信的确是他可信的手书。”他这话说的结结巴巴,连哲德都感到尴尬。哲德不想戏弄他了,于是说:“去把当事人,那家的农民和发现这珍贵手书的僧侣给我叫来吧。我需要分辨事情的真相。”修道院长便使人去找他们了。 等待的时间里,哲德拒绝了修道院长陪伴的要求,借口要看看修道院的风光,独自在修道院里散步。他在那些平整的道路上轻轻地踱着步,低头思考着如何处理这件事,只是偶尔才抬起头来看着教堂屋顶的十字架。甚至连待会的审问都只是一个过场,一个证明他没有偏私的仪式而已。真正的问题是判决会带来怎样的影响。他陷入了两难的选择。并非因为他贪图利益,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才是真正正确的。利弊的权衡并不容易,尤其是要考虑长远。 不久农民和僧侣到了。审判开始了。虽然有先入为主的判断,但他决定还是需要认真审问,以免造成冤屈。那个农民面容黝黑,满脸愁苦。他的躯干壮实,手上、脖子上筋脉毕现,手掌上积着厚厚的茧子。脚上还积着没洗干净的泥土。他的眼睛根本不敢看人,闪闪缩缩,好像在害怕什么。他穿着弗里斯一般平民常穿的短上衣,有些旧了,可是破烂的地方都缝补得很好。哲德问他:“你为什么说那块土地是你的啊?”“啊。”那个农民说话时几乎要哭了起来,“我怎么知道呢?我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块地,我们世代在这里住,在这里耕作。我从记事起爷爷就和我们说他记事时就住在这里了。我们这些穷苦人,目不识丁,又哪里去找什么凭证啊!” 哲德又去问那个年轻的僧侣。他让哲德想起了不久前的自己。哲德问他:“你是怎么发现那封信的?”僧侣在摩挲着双手,目光游离,好像要躲开哲德的视线,然后说: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只是一个修道院的抄写员,我的工作就是抄写古罗马的文本。当我翻开一份古老的羊皮卷时,这封信就出现了。”哲德听完,离开他,走到修道院长身边,忽然大声说:“我觉得你在撒谎!”这把修道院长和僧侣都吓了一跳。僧侣把手放了下来,低着头,没有回应。修道院长说,带着几分威胁:“他是上帝的仆人,不会说谎的。不要再问了,判决吧。”哲德鄙夷地看着他一眼,转过身去。 修道院长继续说:“这些土地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而领主大人是否高兴,你必须知道,也取决于我们。你该好好判决。” 哲德已经想好了,然而他感到非常难过,非常不甘愿。所以他拖了很久,然后才叹了口气,说:“我宣布,这片土地归修道院所有。”农民听到这个判决,当即痛哭起来了。修道院长则很高兴,他让人把农民轰了出去,然后对哲德说:“我们非常满意这个判决,我们会告诉所有人,肯莫尼的雅尔是一个公正又虔诚的人。另外,我们还为你准备了一些小礼物。” 哲德拿到了150先令。这并不能让他快乐。现在他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,罪恶接二连三地到来。 他当然知道修道院为了霸占土地而伪造了这些文件,也希望能把土地判还给农民。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得更多。修道院看上了这块地,那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得到它。他们势力强大,诡计多端。即使农民在这次纠纷中保住了土地,也还会有下一次。而自己是不会再被委任裁决的权力了。甚至那些披着华衣的豺狼,还不知为这点利益,做出怎样叵测的事来呢。那时,那些可怜的农民丢掉的就不止土地了。所以他不得不屈服于现实。这就是政治的残酷,它让人必须妥协。 哲德跟着农民,看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里,宣布那个坏消息。屋子里传来一家人的哭声。修道院的人也跟着来了,他们现在就迫不及待地享用自己的战利品。他们没有一刻等待,马上把哭成一团的农民一家驱赶出来,甚至不许他们带走自己的东西。哲德站了出来,警告他们:“我的判决里,只有土地是属于你们的。让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带走吧!”僧侣们勉强同意了。农民一家于是赶紧拿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可这并不能减轻他们对哲德怨恨,他们盯着他看时,眼里冒出怒火,好像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。孩子们走过他的身边,都要吐上一口口水。 哲德把身上的钱都给了那个可怜的农民。三百先令,这已经是一笔大钱了,足够这个家庭生活一两年。然而这远远不够够呢。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田地,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,何况他们眼前就没有住处了。不过农民接受了这些钱,对他的态度也好了些。 哲德乘机安慰这个可怜人,向他说明自己的难处,并建议他暂时到道琴嘉去租住。还向他承诺一定会给他找到新的生计。这些都是哲德考虑已久的了,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的罪咎。虽然他还没有想到有什么新的生计。 无论如何,农夫重新信任了他,带着一家老小跟着哲德到了道琴嘉。在那里,哲德把这家子暂时托付给了索里克。 “这不会麻烦您很久的。我很快就会找到对策。现在我必须去回报雅尔了。”索里克说:“没关系的。我会照顾他们。去吧。”哲德于是再次离开了。将要分别时,他步履蹒跚,垂头丧气。索里克忽然大声喊住了他,哲德又走回来听他要说什么话。索里克觉察到了哲德的疑虑,因此开解他说:“年轻人,前面的路还漫长的很,不要自己缚住手脚。在我看来,你做了正确的事。须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,许多事是不如人意的。然而我们也无法逃避。当一切都终结时,只有上帝才能裁决我们的价值。”哲德点了点头,走了。
|